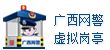岑氏留言
-
岑延旺于2022-10-27的留言:
湖南永州江华岭东一带散布着岑氏,因为文革时期族谱被毁,但是按照广西西林字辈排序,不知道我们是哪里来的了,老一辈说以前跟桂岭一带岑氏族人有联系,进入21世纪后,没联系了……有没有人考证一下。 -
岑卫东于2022-05-13的留言:
岑氏亲人们,大家好!我是岑卫东,是文化大革命时代的“产物”。机缘巧合吧,终于能在这里见到如此多的岑氏亲人们围聚一堂畅所欲言,很是心慰,同时也带着一丝丝的遗憾!因为我还未出生时,爷爷(岑定伍)就不在世了,后来妈妈生我的时候,又遇上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可能是文化大革命复杂的氛围和我俩兄妹当时还小的缘故吧,爸爸(岑国玉)一直守口如瓶,极少对我们兄妹俩谈起他的身世和爷爷的事情,甚至我妈妈都不知道一丁点。再后来,我爸爸有一天突然得了急病,很快就离我们而去了。我现在只有了解到爷爷(岑定伍)有一个兄长,在逃难时失散了(名字不详),之后爷爷就做起了生意,并雇佣了工人协作 他,听说爷爷的生意还做得不错(当时那个时代,我爷爷属于榨取贫下中农的血汗,走资本主义道路,政治身份不良,是要受到批斗和坐牢的)。不知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否找到一点点的线索否?愿上天给我一点希望,也愿能从岑氏宗亲网里能得到一点点的线索。万分感谢!! -
岑炳旺于2022-04-02的留言:
我们想增加人才库,有一位岑氏后裔在南宁二中任副校长,另一位在平乐县交通局任副局长。 -
岑勇于2022-03-08的留言:
祖墓碑文: 莫为之前雖美弗彰,莫为之後雖盛传我,祖之前後,世襲於朝,而受爵者,其历有可纪矣。 一始祖岑公諱彭。汉马功劳擢授廷行大将军乃湖广襄汉南阳始镇也。 一始祖岑公諱世铿。擢授怀远大将军乃溪洞镇也。 一始祖岑公諱永珍。擢授盟威大将军亦溪洞复镇也。 一始祖岑公諱伯颜。擢授田州中顺大夫试也。 一始祖岑公諱永泰。擢授恩州奉训大夫试也。 一始祖岑公諱辉。擢授岜鈴汎官总司守也。 一始祖岑諱光裕。为国亡身,蒙上宪不忍昧功臣,柱碑立祠,以祀之留後。仲述分住于此,只克全後裔分为五枝,有孙国泰初头门庭,继後子孙荣昌。皆由祖德流芳,以及於今孙等,歆潜恐夫特著表於,兹以头不忘之意耳。 -
岑厚霖于2021-11-18的留言:
自从19年我爸过身之后,我就一直没怎么接触岑氏宗亲的事和东西。今天忽然好想我爸,点开了他的微信头像,看到朋友圈,发现了这个宗亲网的链接,就进来看看。我想说 是,家里还有很多我爸当时收集什么关于族谱的资料。不知道有没有人需要?希望能对大家有用,不用放在家里蒙尘。
岑氏要闻
当前位置:首页 > 新闻资讯 > 岑氏要闻
岑毓英与刘铭传办理台防之比较
信息来源:岑氏宗亲网
作者:
更新时间:2009-08-24 17:45:22
岑毓英与刘铭传办理台防之比较
广西师范大学教授黄振南 博士研究生黎瑛
岑毓英(1829~1889)与刘铭传(1836~1895),一为广西人,一为安徽人,分别是壮族名人和淮军宿将,都是晚清重臣。中法战争爆发前,他们分别赴台办防,为后来的台湾抗法保卫战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办理台湾防务的过程中,岑、刘二人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认识台岛的安危,以保家卫国为己任,或前后师承,或相互衔接,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由于时间、条件等方面的差异,岑、刘二人在具体办防的出发点和具体做法方面都有诸多不同。本文抛却其中的共性,通过比较寻其承继关系和差别,进而分析差别产生的原因,探讨两人对台湾防务的贡献,并籍此求教于方家。
一、办防的承接关系
中法战争前夕,为了加强台湾的军事实力,光绪七年四月初八日(1881年5月5日)清廷诏令岑毓英任福建巡抚,办理当时隶属于福建的台岛防务。从光绪七年七月初五日(1881年7月30日)抵达福建省城,到翌年六月十二日(1882年7月26日)离闽赴任署理云贵总督,岑毓英在闽办理台防时近一年。中法战争爆发后,台海告急,刘铭传奉旨以巡抚衔督办台湾军务,从光绪十年七月十六日(1884年9月5日)抵达基隆起,刘铭传在台几近7年之久。岑、刘二人前后受命赴台办防,在实际工作中有着明显的承接关系。
1.开山抚番:岑打下基础,刘添砖加瓦
随着汉人的一批批迁入,台湾岛上的原住民在人口比例中变成了少数。岑、刘赴台前后,台湾的少数民族被称为“番”,其社会发展程度相对落后。按其发展程度的高低,这些少数民族又有“生番”、“熟番”之别。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台湾的少数民族被迫栖身于高山密林中,与汉族人民形成一道深深的鸿沟,民族间的政治、文化联系几乎处于断绝状态,严重阻碍台湾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尤其是中法战争爆发前,因闽、粤汉人的涌入,民族矛盾激化,直接影响到台湾的防务。鉴于台湾民族关系复杂,民族团结受到影响,岑毓英、刘铭传都致力于开山抚番,通过调理民族关系,藉以加强防务。
台湾民族关系的紧张和改善民族关系的必要性,有记载说:“生番横亘南北七百余里,与民地相交错,年戕民命至千余。匪盗则藉番地以出没,聚众抢劫;土豪则藉防番以敛费,养勇抗官。号令不行,赋税不清,值时多故,内患不除,无以御外侮。”[1] 此外,因阻隔前、后山的“番社”与汉人关系不睦,台北、台中两路防军巡逻时只好绕过这些“番社”,路途袅远,行军不便,运送粮米、军火尤难。岑毓英抚闽之前,清政府已经注意到台湾民族问题的严重性,并就“开山抚番”做了一些尝试,但未达到预计目的。故在调岑毓英任福建巡抚时,清廷特别强调:“其开山抚番未尽事宜,亦当体察情形,次第经理,以为远久之计。”[2]岑毓英身为少数民族,出生于少数民族地区,又在广西、云南、贵州等多民族杂居地任职,深知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性。故一到台湾,他便开展民族调查。并“饬何秀林、邓复胜等,俟开年春暖瘴轻,即设法将路开通,并清查各番社。凡就抚番目,按所管番户多寡,给予八九品顶戴。月给饭食银数两,责令约束番民,懔遵教化,果能相安无事,再仿照湖南凤凰三厅成案,奏请分设千把、外委各土职,以示鼓励。”[3] 其目的在于调理好民族关系,壮大抵御外敌的力量。
在派员深入少数民族地区“招安”、开路的基础上,岑毓英还积极做好屯弁缺额的工作。他亲自“调集考拔,咨部注册”;同时加强训练“归顺”的少数民族青壮年,使之成为既能下地耕作,又能操枪打仗的战斗集体。当时台北、台南的“熟番”共有4 000名,岑毓英从中挑选1 000名,委员管带操防,“以三月为期,轮流更换,不致废农。原领饷银照旧发足,在防之日,加给口粮,所费亦属不多,于开山抚番颇有裨益。” [4] 岑毓英的努力没有白费,这些番民后来在抵御外侮的斗争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如抗法主要战场的“沿海八县之地,番居其六,民居其四”,[5] 且因高山族人民“矫捷敢死”,抗法将领们认为“可资其力以抗寇”,“务须格外设法抚使可用。”
在岑毓英开山抚番的基础上,刘铭传继续抚番,他认为加强招抚山中少数民族是巩固台防的重要措施之一。他自兼台湾抚垦大臣,以当地有名富豪林维源为帮办,设抚垦总局,将全台部落地区分为三路:埔里以北至宜兰为北路,以南至恒春为南路,台东一带为东路,各置抚垦局及分局,积极开展招抚民众和开拓“番地”的工作。在1886~1887年间,后山各部共招抚“番社”280个,“番丁”5万余人,前山各路260余社,“番丁”3.8万余人,“水尾、花莲港、云林、东势角等处,可垦水旱田数十万亩。”[7] 对于前、后山以外的少数民族,也分别就划定界限、定期交易等问题成立协议。这种新关系的建立,对于扩大各族人民之间的接触与交流,增强民族团结,联合各民族力量办防,具有积极的意义。
此外,刘铭传还致力于发动各“生番”、“熟番”奋起抗法 ,使富有战斗精神的少数民族同胞踊跃参战。如林维桢率领的“南番屯军”,“系招募南路生番,参与粤勇。” 各族战士精诚团结,把仗打得十分出色。沪尾一战,内山张李成领导的500名少数民族战士“散发赤身,嚼槟榔,红沫出其吻”,[9] 他们一分为二,分别埋伏在擢胜军之后,擢胜军与敌接仗溃败后,前面的250人“见敌皆仰卧,翘其左足,张趾架枪以待敌。敌近,二百五十枪齐发,法人死者百数,大骇而循。山后复出二百五十人,作圆阵包敌,”[10] 把法军赶下了海,体现出少数民族在抗法斗争中的英勇善战。
应该说,在安抚少数民族方面,刘铭传的做法是岑毓英的继续。尽管岑毓英和刘铭传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台湾的民族问题,但在战争即将来临的关键时刻,他们前后相接的“开山抚番”政策,对于缓和内部矛盾,联合各民族力量一致对外,在抗法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2.海防:岑修筑炮台,刘续修并守御
岑毓英到台后,经过实地考察,发现台湾港叉纷歧,四面受敌。基隆、沪尾等口虽有炮台,但不足资捍卫台湾。台北、宜兰各县尚无城垣,很可能会被敌人从此地进攻,从后路袭击台湾,于是加强防务建设成为当务之急。为此,岑毓英在观音山等处监修了一批炮台、营碉,在基隆添修了1座炮城,15座碉楼,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台湾的防御能力。在任云南、贵州巡抚时期,岑毓英先后在滇省铸造开花大炮56尊。为了加强台防,他奏请将这56尊开花铜炮由总兵雷应山、余寿康,副将王家彬保护运往福建台湾,以加强台湾的防务,清廷批准了他的奏折。
在岑毓英建设的基础上,刘铭传也加强海口炮台的设置。他在澎湖设4座炮台,分别安置于西屿东西、金龟头、大域北,这样使澎湖防务面貌一新;在基隆,刘铭传聘德国技师重建基隆炮台,在基隆、沪尾各设炮台2座,台南地区安平旗后,大坪山各设炮台1座,高雄四座。同时用铁、水泥加固安平、旗后、沪尾、妈宫、西屿、大城北诸炮台,配备以阿姆士顿大炮31尊,沉雷60,碰雷20,火力比前增强数倍。他还购置火力大的新式钢炮装备炮台,以沉雷、碰雷分布各海口,使炮台防守力量得到加强。为了防止敌军封锁,他又在台北设立军械机器局,聘请外国技师,利用台产硝磺,以小机器厂制造枪弹,大机器厂制造炮弹,并设立军械所为储存之所。此外,刘铭传在大龙峒设火药局。在基隆、沪尾设水雷营,更设转输局于上海,以运输兵器及其他军用物质。在他的大力整顿下,台湾防务日渐充实,比过去前进了一大步。
3.陆防:岑调兵守台,刘扩充调整
岑毓英接到赴闽筹办海防的命令后,即意识到闽疆重地,防务紧要。他深感“用兵之道,必使将识兵心,兵识将意,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方能运调自如。”[11] 他考虑到初到福建,对那儿的将弁优劣缺乏了解,担心在仓促之际用人不当,致使贻误机宜。因此岑毓英在滇黔省练军中的安义、松桃等营内挑选精锐士兵2 000名作为亲军小队调往福建,但不露调兵名色,旨在“于防备之中,仍寓镇静之意。”[12] 这些黔军到台后,使台湾的兵力扩充到1.1万多人。除留守澎湖、各海口和前、后山外,岑毓英将这些兵力分为3部分:一部分驻扎台南;一部分驻扎台北;另外一部分驻扎台中之彰化县。在黔省还有一些著名将领,如提督衔记名总兵雷应山、松桃协副将杨国宝、记名总兵请补黎平营、参将丁槐、记名总兵云南楚雄协中军都司张继声、总兵用留黔补用副将何秀峰等,他们均是身经百战、可以独当一面的将领,岑毓英将这些可用之才陆续分带赴闽,以备调遣。这些优秀将领和精锐士兵的到来,为台湾防务注入了新的活力。
刘铭传接管台湾后,对兵力大力整顿,妥定军制,裁减募勇,剔除绿营积习,汰弱留强,认真训练。刘铭传还请求朝廷严格赏罚,考察操练枪法,以求将才。他说:“朝廷整顿武备,物色将才,必先实技,或枪炮命中,或操练优娴,或明中国地舆,或悉外洋战法,身体强健,才略深长。”[13] 台湾40营防军,经严汰老病之后,刘铭传只留35营,全部改用洋枪,“严肃营规,认真操练”,[14] 并聘请外国教习,加强训练。他废除以前的绿营旧规,改为勇营制度。重新部署兵力,以定海4营驻北路,铭字4营驻基隆,栋字3营驻中路,练勇4营驻南路,镇海8营驻后山,宏字4营及水师驻澎湖。在台北设团练总局,各府、县、厅设分局,各乡没团,分段自卫,维持治安。
二、防御策略之异
前后继承既表现在岑毓英与刘铭传办理台防的时序上,又反映在两人办防的某些做法中。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两人在办防过程中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差异,防御策略不完全相同便是其中之一。
1.岑通盘考量,刘突出重点
岑毓英接到任命后抵台,经过实地调查,他认为,“台湾地方孤悬海外,日本窥伺已久。不早筹整备之方,则戒心易启;不量予变通之策,则兵气不扬。”[15] 通过实地深入调查,他发现台湾自北而南,沃野数百里,粮食、茶、糖、煤炭皆出其间,海滨居民,有渔盐之利,前、后山又出樟脑、硫磺及各种竹木,可谓得天独厚,难怪外国侵略者垂涎。而且台湾防务与内地不同,内地各省仅一二面临海,所备者寡;台一孤岛,港叉纷歧,四面皆为受敌之区。基隆、沪尾等口虽有炮台,但不足资捍卫台湾。台北、宜兰各县尚无城垣,战争中敌人常常出其不易,攻其不备,因此敌人很可能由无炮台之处舍舟登陆,抄袭后路登台。而台湾自归版图以来,屡有变乱。这些都是办理防御的难点。综合各方面的考虑,岑毓英认为,“台湾之事,当以省刑薄敛,固结民心为上;分路屯兵,严守陆地次之;添扎营垒,保守海口炮台又次之。而三者俱宜相辅相行,不可偏废。”[16] 这是岑毓英经过亲身调查,周密研究之后得出的筹办台防的总设想。
这个设想打破了单纯的军事防御观念,熔政治、经济、军事于一炉,是岑毓英军事思想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其中,把减轻老百姓负担,团结台湾各族人民放在首要的地位,表现了他在办防中紧紧抓住了人这个重要的因素,突出了人在战争中的主导作用。以是言之,岑毓英强调团结,依靠民众;守陆地和保海口既要有主次之分,又要相辅而行,不得偏废,是他实地勘探,精心研究的结果。
而刘铭传则主张对台湾实行重点设防,同时兼顾台湾岛上其他重要海口的防御,形成一个有主有次、合理的防务体系。这是刘铭传台湾防务思想的重要内容。他指出:“综计全台防务,台南以澎湖为锁钥,台北以基隆为咽喉。澎湖一岛,独屿孤悬,皆非兵船不能扼守。”[17] 这一重点设防主张可概括为“南澎北基,澎岛尤重”。台湾四面环海,海岸线全长千余公里。台湾西部海岸是平坦的沙滩,东部海岸是悬崖屹立的山脉。台湾这种地形,客观上为刘铭传在台湾实行重点设防提供了客观依据。
从策略上看,岑毓英关注更多的是全局性的问题,刘铭传则把问题细化,表面上有不少差别,实际上目的是一样的。
2.岑关注民生,刘强调治兵
为增强台湾防务实力和提高台湾防务效能,岑毓英将争取民心放在防务建设的首位。他围绕台防所进行的主要是一些传统的民本措施,如整顿吏治,赈济灾民,调理民族关系,等便民方案。光绪七年(1881)春夏之交,台湾部分地区叠遭地震和飓风、大雨的袭击,影响较大的就有4次。数次自然灾害,对澎湖地区影响尤巨。因为这里不适宜种植禾麦,老百姓全望花生、地瓜等生活,而这些农作物在生长期频繁遭受烈风狂雨,藤叶根株大都霉烂,有碍收成。眼看成千上万的人将要背井离乡,逃荒要饭,身为福建巡抚的岑毓英深表怜悯,批示由原台湾道升任福建臬司的张梦元筹拨粮米赈济。张即从义仓谷中提出2 000石碾米运往赈济。他又令新任台湾道刘璈从台局货厘项下提银5 000两,派人携往浙江温州府采购薯丝、小米等物资加以接济。考虑到当时彭湖列岛饥民达8万余众,这些粮米不敷发放,岑毓英又奏请从福建省城增广仓义谷中提陈谷2万石碾米前往救济。岑毓英的奏请得到了清廷的批准,令他“妥为赈济,毋任所失”。嗷嗷待哺的饥民即得救济,并得以重建家园。
同年12月,台湾的彰化、嘉义县由于逼近海边,亦叠遭狂风暴雨,所种杂粮,收成歉薄,饥民甚多。岑毓英了解实际情况后,即饬该县官绅,分别周济。他雇佣年轻力壮者来修大甲溪河堤,以工代赈;对于众多老弱病残及不能工作的妇女,他则饬司道将省城增广仓存谷酌提碾米,运往赈济。岑毓英的这些安抚措施,体现了他为民着想的精神。在国家内忧外患之际,通过重视安抚,尽可能减少内乱,加强边疆的防务,这无疑是岑毓英防务建设的出发点。
极力推进与防务建设有关的近代化建设,是刘铭传台湾防务的基本内容。他着眼于增强台湾防务实力,建设了一系列的军事设施,逐渐形成台湾的军事经济体系。刘铭传非常重视军事设施的建设。他强调“海防以船为命,无师船即无海防,各国皆然,中国岂能独缓”。[18] 因此,要加强海防,就必须首先添购兵轮。同时,应改建沿海各炮台,以加强防守。但除了要有坚实的炮台,“尤须炮利”,因此他主张筹购和自造大批枪炮,以节省经费。他请求总理衙门会同北洋大臣李鸿章,筹款四、五百万两,派熟悉洋务、精通枪炮人员,赴西洋各厂订购枪炮,并建议用中国本土材料,开台湾铁矿,采后山木材,自造枪炮,推广制造之学使制造技术逐步提高。当然,还得对这些军械加强管理严格稽查军械,于是他设军器局,统一管理军械。
抵台后,刘铭传多方筹款,相继购买了“威利”号、“威定”号、“南通”号、“北达”号、“前美”号、“川如”号等兵轮。光绪十二年正月,各口炮台开始兴工建筑。到光绪十四年,澎湖、基隆、沪尾、安平、旗后5海口共造炮台10座,,并且配备英制阿马士庄大炮31尊。为了加强炮台防守的能力,还配置了水雷。在刘铭传的主持下,台湾先后购买后膛洋枪1万多杆,极大地充实了台湾的国防力量。光绪十一年三月,刘铭传饬令记名提督刘朝干在台北大稻埕建造军械机器局,创办了台湾第一个军事工业。机器局自制弹药、枪弹和炮弹,聘请德国人彼德兰为工程师。此外,刘铭传在大隆同设立火药局,以淡水所产的硫磺为原料制造火药。又在基隆和沪尾两地设立水雷和水雷营,制造和安设水雷。台湾自制枪炮使台湾的军需基本上达到了自给自足。
3.岑立足台岛,刘主张联防
台湾“悬于海上”而又与中国大陆一水之隔,岑毓英早就意识到,台湾的防务是中国海防的关键,台湾的存亡直接影响到大陆的安危。1881年岑毓英赴闽任职时,就首先视察台湾。他在《会商台湾防务大概情形折》中写道:“台湾地方孤悬海外,日本窥伺已久。不早筹整备之方,则戎心易启;不量予变通之策,则兵气不扬。臣毓英奉命督办,责无旁贷,惟有懔遵圣训,随时亲往查勘,认真经营。”[19] 因此,岑毓英的防务建设立足台岛,他将滇、黔的精兵强将调入台湾,将其进行合理的规划,加强台岛的兵力和军需。此外,他强调团结,依靠民众;守陆地和保海口既要有主次之分,又要相辅而行,不得偏废,在全岛形成一个积极向上、一致对外的局面。
而刘铭传针对台湾设防,则主张台湾防务以大陆为依托,实行“台闽联防”。这是他台湾防务思想的核心内容。1885年7月,刘铭传根据在台一年的考察,向朝廷上《条陈台澎善后事宜折》,明确提出了“澎厦联防”的主张。他说:“臣到台一年,综观全局,澎湖一岛非独全台门户,实亦南北洋关键要区。守台必先守澎,保南北洋亦须以澎厦为莞钥。澎厦驻泊兵轮,防务严密,敌船无能停泊,万不敢悬军深入,自蹈危机。此澎厦设防,实关系全局,非仅为台湾计也。”[20] 刘铭传的这一防务思想,是从中法战争教训中取得的,又是战争教训的理性化。
在中法战争期间,清廷在上海设立台湾军械粮饷总局、转输局,专门向台湾输送军械粮饷。大陆人民,特别是海上渔民,更是冒着生命危险,运兵、运械到台湾。法军封锁期间,大陆共向台湾输送了军队2 000余人,白银70余万两,另外还有大量枪支弹药。这些援助缓解了台湾军民在抗法斗争中的军需供应紧张问题。实际上,没有大陆尤其福建的支援,台湾防务必然是无本之木;失去台湾的屏蔽,福建的战备也难以稳固。两地唇齿相依,唇亡则齿寒,基于这一认识,是刘铭传才提出联闽防台,建设台湾防务。“全恃闽疆为根本,声气联络,痛痒相关”,[21] 甚至为了加强台闽两地的联系,刘铭传曾经上书清廷,反对将台湾从福建划出单独建省,“司道以下,畛域分明,势必不相关顾。”[22] 清政府否定了刘铭传的这一建议,但对他联闽防台的思想给予了肯定,指出“台湾虽设行省,必须与福建联成一气”,“庶可内外相维”。台湾建省后,刘铭传非常重视与福建合作,他和当时闽浙总督杨昌浚经常就两省防务及其他建设问题交换意见,1886年7月14日,杨、刘二人联衔上奏《遵议台湾建省事宜折》,折中再次明确了台闽联防的基本原则,“闽台本为一省,今虽分疆划界,仍需唇齿相依,方可以资臂助。应遵旨内外相维,不分畛域,乃能相与有成。”[23] 而且福建每年还向台湾提供白银45万两。福建的支持和帮助,为刘铭传的防务建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条件。
三、防务措施之别
在不同的防务策略指导下,岑、刘二人的防务措施也不尽相同,其主要表现如下。
1.增强实力:岑兴修水利,刘筑路办矿
在福建巡抚任内,兴修水利是岑毓英加强防务,增强实力的一大举措。他看到彰化、新竹两县交界之大甲溪,地当冲要,每遇春夏之交,溪水泛滥异常,田地多被冲没,遭溺的行人,亦复不少,久为地方之患。于是他筹款修筑大甲溪河堤,开挖河道,以溪中乱石,和篾笼间杂铁笼装筑长堤,形如八字,将各股溪水束归河中流入海,使大甲溪舟船能过,不再危害人民。为人民的生活、生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此外他还另开堰沟,以溉田亩,并将两岸荒地招佃开垦,促进了台湾农业的发展,于民生实有裨益。
而刘铭传着眼于增强台湾防务实力,进行了一系列近代化建设,逐渐形成台湾的军事经济体系。如修筑铁路,开办矿务,创立制造局等。1887年4月27日,他上奏朝廷,明确指出在台湾修筑铁路“有裨于海防”,因为,台湾“新竹、彰化一带海口纷歧,万无此兵力处处设守”,“如遇海疆有事,敌船以军队猝然登岸,隔绝南北声气,内外夹攻,立见危迫。若修铁路,调兵灵便,何处有警,瞬息即至,无虞敌兵由中路登岸。”[24] 1889年3月在《复陈津通铁路利害折》中,刘铭传再一次指出:“台疆千里,四面滨海,防不胜防。铁路一成,则骨节灵通,首尾呼应。”[25]
当奏请在台湾修筑铁路获准后,刘铭传便在台湾设立铁路关局,聘请德籍工程师毕克尔为监督,向民间发行铁路股票,自1887年7月开始修筑。经几年努力,至1893年12月,筑成台北至基隆、台北经台南至新竹两段铁路,全长约100公里。
早在赴台前夕,刘铭传即于1884年6月上奏《遵筹整顿海防讲求武备折》,条陈海防十事。其中一事为“稽查军械,整顿矿务,宜特设军器局,切实经营,以专责成。”他认为:“制造为自强之本,矿务为制造之源。”[26] 刘铭传在抚台期间,极力将这一思想付诸实践,力图通过开办矿务,创立制造局,建立近代化的国防体系,以强化台湾防务实力。他在抚台6年中,设立煤务局,恢复基隆煤矿;创立台湾军器局,开办台湾大机器厂,独立制造和修理枪炮子弹。此外,还设立军装局、火药局、硝药局、水雷局、转运局等。
2.军事设施:岑重台北,刘重澎湖
在做好安抚工作,团结民心,一致对外的前提下,岑、刘二人的防御重点也各有千秋。岑毓英将战略防御重点放在台北,他在此增添了许多军事设施,如在观音山等处监修了一批炮台、营碉,以防止来犯之敌直插台北府。而基隆又是台北设防的要害之区,是从海上进犯台北的通道,这里有提供船舰停泊的港口,还有年产5万多吨的煤矿。失去基隆,意味着把军事基地和军舰所需的燃料让给外敌,事关大局,故有台湾“近防三林、鹿子,远控淡水、基隆”之称。[27] 因此基隆军事设施的添设,是岑毓英台防中最大的一项。他添修了1座炮城,15座碉楼,并从贵州铸造的56尊开花铜炮中拣选8尊安置在基隆防御工事上,使之有台有炮,防守自如。
而刘铭传把设防的重点放在澎湖。他认为:“全台各海口,大甲以南至凤山,沙线辽澎湖阔,兵船不能拢岸,远隔四五十里,近亦二三十里,设防较易。而大甲以北,新竹一带海口纷歧,直至宜兰,至远不过三五里。基隆、沪尾虽能停泊兵轮,尚多山险,如有水雷巨炮,设防尚有余力。惟新竹沿海平沙,后垄中港皆可出入3号兵船,地势平衍,全恃兵力,颇难着手,然犹较胜于澎湖。”因此澎湖 “不独为全台之门户,亦为南北洋之关键”,“欲守台湾,必先守澎湖,欲保南北洋,亦必先保澎湖。”[28] 为此,他将训练有素的宏字3营驻守在澎湖,并把守将级衔由副将提升为总兵。3营水师分驻于妈宫、嵌里、八罩、将军澳、西屿等地。增设炮台4座,配各17尊阿马士顿后膛炮以及若干加农炮;他还将台湾当时仅有的一艘“海镜”号兵舰专供澎湖驻军差遣,添购“威利”号、“威定”号、“飞捷”号、“南通”号、“北达”号等一批兵轮商船,以加强海上防御力量;在澎湖妈宫依山凭海处构筑城堰,等等。这一系列时防务建设,大大地增强了澎湖抵御外敌入侵的能力。
岑毓英在治理台防的时候已经意识到澎湖防守的重要性。“澎湖一岛,乃台郡之门户。门户固则堂奥清宁。是所谓扼寨之大者,澎湖若也。”[29]“台湾环海依山,延袤二千余里,择其要而扼之,择则莫若澎湖一岛。” [30] 遗憾的是,他来去匆匆,未来得及在澎湖添设必要的军事设施,仅将保障澎湖人民的生活作为台湾防务的一个重要前提。而刘铭传弥补了这个遗憾,在岑毓英台防的基础上,他将台湾防务进一步完善。
经过几年的努力,在岑毓英建设台防的基础上,刘铭传基本上建起了陆地、海口、海上相结合的近代化防御体系。这使台湾,尤其是在台北、澎湖等地增加了防御层次,拓宽了防御领域,加强了防御的稳固性,从而使台湾的防御空间大大延伸,对维护国家主权,巩固祖国的统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差异存在的原因
诚然,无论从其防御规模和投入而言,岑毓英与刘铭传是无可比拟的。这是由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深刻的内在因素所造成的。
1.办防形势不同
1874年,日本借琉球船民被高山族人杀害的事件,武力侵台。由于清政府苟安软弱,在双方力量对比完全有利于中国的情况下签订《台事专条》,日本获得50万两赔款。这一让步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侵略野心,认为在东亚耀武扬威的时刻到了。1879年,日本废琉球蕃,改为冲绳县,将其正式吞并。显然,台湾成为日本侵略者所觊觎的地方。中法战争前夕,加强台湾的防务力量引起清政府的重视。在清朝的众多大臣中,岑毓英的骁勇善战颇得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光绪七年四月初八日(1881年5月5日)清廷的“上谕”云:“台湾为南洋门户,防务紧要,日本前议琉球一案,未允所请,该使臣悻悻而去,难保不藉端生衅,自应思患预防,严行戒备。岑毓英历久戎行,谙习兵事,即著责成该抚臣将台湾防务悉心规划,与何璟会商布置,务期有备无患。”[31] 当时台湾尚未建省,隶属福建,形势的紧迫决定了岑毓英接任福建巡抚的主要职责是经营台湾,督办台防,防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然而遗憾的是,中法战争爆发,西南边疆危在旦夕,因此岑毓英又被匆忙的赶回云南,台湾的防务也被迫放下了。
刘铭传任台湾巡抚时,中法战争已经爆发。法舰进逼台湾,南中国海战云密布,清廷“两宫宵旰忧劳,其时内外臣工,无不以台湾无备为恨。”[32] 1884年6月,清政府诏任前直隶提督刘铭传以台湾巡抚衔,督办台湾防务。刘铭传临危渡台,在广大爱国军民的支持下,取得了基隆保卫战的胜利,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法军决计攻闽江下游的第三重门户——马尾军港,企图破坏福州船政局,结果马尾海战福建水师全军覆没。福建的严重挫败,使台湾失去了隔海的犄角之势,台湾局势十分危急。但刘铭传在严酷的鏖战中又取得了沪尾大捷,法军从此不敢轻易上岸,而是利用海军优势封锁台湾海峡,妄图切断大陆对台湾军民抗敌斗争的援助。清政府在台湾抗敌军民的强烈要求下,也采取了种种驰援措施,但收效甚微。1885年2月,援台南洋五船,在浙江洋面被法军截击。3月,奉命支援福建前线的部队,因为无船东渡,只得坐失战机。4月,渡台的清军700余人在澎湖附近被栏截,虽然刘铭传在大陆军民的支援下,获得了一些物资供应,对抵制法军的封锁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这种“偷渡援台毕竟缓不济急,且损失过重”,[33] 台湾的局势依然没有重大转机。
刘铭传就是在这种艰难的局势下任治理台湾防务,他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坚守8个多月,使“孤岛卒存”,因此他对台湾的防务有更深刻的体会和更清醒的认识。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决定建台湾省,抗法有功的刘铭传即充任台湾第一任巡抚,他把台湾的防务更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2.任职长短不同
清廷派岑毓英治理台防,时间不足1年,来去匆匆,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防务建设,只是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面对随时而来的外敌入侵,岑毓英防务措施的核心必然是在台湾百姓的生计上,帮助各族军民克服生活上的种种困难,造就全岛民心所向的局势,为即将来临的反侵略战争做好准备。
而刘铭传的台防建设主要在中法战争后期,他是台湾建省后的第一任巡抚,抚台近7年,有条件对台湾进行全方位的防务建设。在这近7年中,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进入了黄金时期,台湾也形成了比较稳固的防务体系。
3.个人阅历不同
当欧洲经过了中世纪的黑暗年代,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中国仍然停滞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下,封建的生产关系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中国的科学技术、生产力发展水平与西方逐渐拉开了距离,而与此相应的军事技术、军事思想等也没有完成近代化的转变。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证明了惟我独尊、夜郎自大的思想已经破产,故步自封只能是自取灭亡,大刀长矛是无法与坚船利炮相匹敌的。一些有识之士深刻地指出,中国要扭转积贫积弱的状况就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发展壮大自己,用以抵御他们的侵略,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口号,倡导学习外国制造战船、火器的先进技术和养兵练兵之法,“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以改变中国军事落后的状态。
刘铭传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他购买了许多西方书籍和报刊的中译本仔细阅读,特别注意探讨西洋科学文化知识。并同一些洋务里手和改良主义思想家交往甚密,同他们共同探讨治国治兵方略,从中增益学识。加之自己丰富的对外斗争实践经验,更使他意识到清政府不思自强,遇事迁就,终非长久之计。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认为“国不变西法,罢科举,火六部例案,速开西校,译西书以厉人才,不出十年,事不可为矣”。[34] 他还与一些守旧派的官僚进行论争,建议光绪帝能够“改弦易辙,发奋为雄”,[35] 希望皇帝能够多读西书,变西法,使中国自强自立。而且刘铭传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并没有停留在“船坚炮利”这样一个层面上,而是比较全面地了解西方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这使他开拓了眼界,在建设台湾防务的过程中尤其是军队的建设中,刘铭传对于“夷技”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而岑毓英是个中规中矩的封建士大夫,长期任职在祖国的西南边疆,他对西方资本主义有着一种本能的排斥。在云南任职期间,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出发,反对侵略者以种种理由进入云南,是岑毓英边疆防务思想的重要内容。其始终认为,洋人来滇,断非好意。免除衅端的办法,就是不让他们进入。对英法两国想在云南通商,他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后来,他重返云南筹办边防的时候,这种态度才改变为“通商可许”。但是,对于滇省厂利,直到临终前,他都抱着断绝英法染指的态度:“彼族藉口通商,实系垂涎厂利。臣等现已将厂务整顿,遴委官绅分投开办,使彼无可争之利,亦足伐其觊觎之谋。”[36] 岑毓英对于西方列强的这种态度,在近代历史潮流中是一种比较消极的、保守的思想。
此外,岑毓英对西方文化还存在一种恐惧,他曾发出“通商之患小,传教之患大,越南教民可为殷鉴”[37] 的忧虑。因为他不仅看到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经济利益的掠夺,还看到西方文化有可能像吞噬越南一样,吞噬着中国。这是两种文化的正面交锋,岑毓英深刻感受到西方文化通过传教士长期的潜移默化,也会征服东方文化。他一生以“士不辱先,斯不负国”[38] 作为个人立身之本,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士大夫。因而对西方文化的渗透,表现出一个民族主义者的强烈感情。因此他没有过多的“洋务思想”,更不会学习西方,进行与之有关的近代化建设。因而无论从台湾防御的规模或投入而言,岑毓英与刘铭传是无可比拟的。
五、结语
岑毓英、刘铭传都先后筹办台防,曾为保护祖国这块神圣的领土殚精竭虑。中法战争是对他们两人办防理论及实践的检验。岑毓英在布置台湾防务时,他将原有的防军扩充到了1.1万余名,除留守澎湖及各海口、前后山外,其余分为3小军,分扎台南、台北和中路之彰化县。其粮饷军火,亦分屯3处,以备急需。根据台湾四面环海的特点,岑毓英对各海口的防御工事给予足够的重视,在基隆海口,他命令修了1座炮城、15座碉楼,并增设台北府城及观音山等处一批炮台营垒。所有这些,都为后来刘铭传等人领导台湾民众抵抗法军的进攻做了必要的准备。
刘铭传临危渡台,在广大爱国军民的支持下,取得了基隆保卫战的胜利,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在福建水师全军覆没,福建严重挫败,台湾失去了隔海的犄角之势的危急情况下,刘铭传仍在严酷的鏖战中取得了沪尾大捷。可见,岑、刘二人的防务建设在中法战争中经受住了现实的检验。
中法战争前岑毓英的台防建设为刘铭传的治理和防务提供了必要的铺垫,他们对台湾的建设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岑毓英的西方文化观,与刘铭传所崇尚“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革进取思想相比,显然仍是一种传统的保守思想。因为世界历史运动的规律性集中表现于它紧紧围绕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的发展,这两根中心主轴是不断向前运动发展的。将岑毓英和刘铭传在台湾防务建设中的所作所为进行比较,岑毓英显得保守一些。
马克思说,人们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个人活动受历史条件的制约。我们评价个人对历史的贡献不应忽视时间、背景、条件等因素。我们只能把岑毓英、刘铭传放在时代的背景中进行恰如其分的比较评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中法战争前后,岑毓英、刘铭传的防务建设有效地保护了台湾,他们对台湾的建设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注释:
[1] 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册中,页1181,中国书店1984年版。
[2]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页1075,中华书局1953年版。
[3] 岑毓英:《岑襄勤公遗集》卷15,页36,光绪二十三年(1897)武昌督粮官署刻本。
[4]《岑襄勤公遗集》卷1,页32。
[5] 刘铭传:《刘壮肃公奏议》卷2,页26,光绪三十二年(1906)刻本。
冯用等:《刘铭转抚台前后档案》页58,台湾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
[7] 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卷24上,页40 《刘铭转抚台前后档案》页57。
[9] 阿英编:《中法战争文学集》页463,中华书局1957年版。
[10]《中法战争文学集》页463。
[11]《岑襄勤公遗集》卷16,页42。
[12]《岑襄勤公遗集》卷16,页42。
[13] 汤子炳:《台湾史纲》,第46页。
[14] 汤子炳:《台湾史纲》,第46页。
[15]《岑襄勤公遗集》卷17,页10。
[16]《岑襄勤公遗集》卷17,页20。
[17]《刘壮肃公奏议》卷3,页18。
[18]《刘壮肃公奏议》卷2,页15。
[19]《岑襄勤公遗集》卷17,页10。
[20]《刘壮肃公奏议》卷2,页26。
[21]《皇朝咸同光奏议》卷39,页50。
[22]《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221,页60。
[23]《刘壮肃公奏议》卷6,页20。
[24]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册6,页190,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
[25]《刘壮肃公奏议》卷2,页16。
[26]《刘壮肃公奏议》卷2,页10。
[27] 范咸等:《重修台湾府志》册中,页1402,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
[28]《刘壮肃公奏议》卷2,页16。
[29] 蒋毓英:《台湾府志》册上,页242,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
[30] 高拱乾等:《台湾府志》册中,页575,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
[31]《光绪朝东华录》页1074。
[32]《刘壮肃公奏议》,卷2,页49。249页。
[33]《中国军事通史》第17卷,第826页。
[34] 陈澹然:《刘壮肃公神道碑》。
[35] 陈澹然:《刘壮肃公神道碑》。
[36]《岑襄勤公遗集》卷12,页1。
[37]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8,页13,民国二十五年(1936)排印。
[38] 赵藩编:《岑襄勤公年谱》卷15,页32,光绪己亥(1899年)刻本。
 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0132号
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0132号